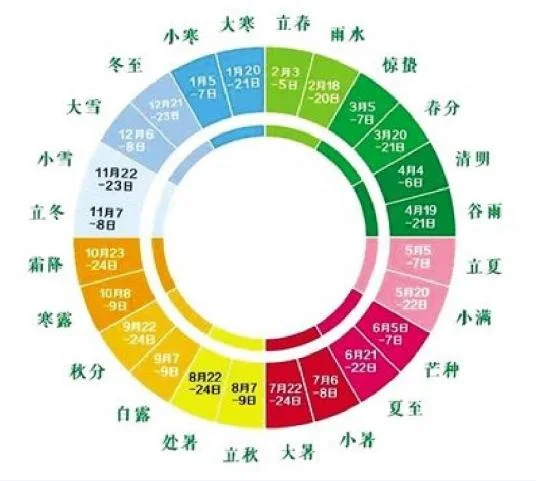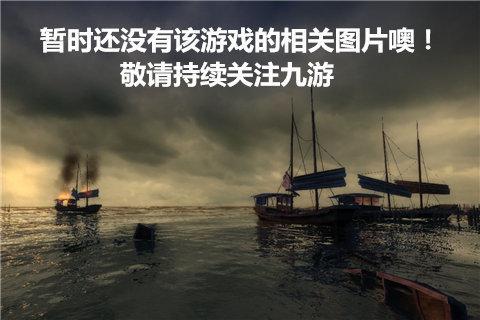司马光和王安石谁是对的(司马光和王安石谁好谁坏?司马光和他的《资治通鉴》)
司马光和王安石谁是对的
1、他俩都是对的,只是出发点不同;2、相比较来说,王安石的观点更符合当时的社会环境。
司马光和王安石谁好谁坏?司马光和他的《资治通鉴》
司马光和王安石都是北宋时期非常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两人都是北宋的宰相,是当时的中流砥柱人物。
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虽然他们之间没有对立,但政治立场的不同仍然使他们处于对立状态,他们一生都在为自己的政治理念而斗争。
司马光和王安石,都是历史名人,都是近代以来后人敬仰的先人。但是围绕着两个人的政治斗争,有人一直在追问。这两个人谁对谁坏?
这个问题其实不太准确!说实话,虽然司马光和王安石的政治理念不同,但校易搜能负责任地说话。司马光和王安石都是为百姓着想,为国家着想的好官。两人都是可敬的君子,无论论功德还是私事,都值得大家敬佩。两个人之所以站在不同的对立面,完全在于政治理念的不同。
北宋宋神宗时期,虽然国力相对强大,但实际上已经开始衰落。北方草原民族连年入侵,不仅威胁到宋朝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也威胁到北宋王朝的统治。最重要的是,为了抵抗这些草原民族,朝廷投入的军队和军需大大增加了中央 *** 的压力。
宋神宗是一个有想法的皇帝。他希望自己能像老祖宗一样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不要陷入这样受人欺负的境地。而王安石呢?他也是一个有抱负、有责任心、实践能力很强的朝臣。
一个有想法做出改变,另一个一直在思考改变计划,希望在未来通过政治改革将国家带入另一个繁荣时期。就这样,你我走到了一起,共同执行改革措施。这次变法就是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因为是在宋神宗熙宁时期进行的,所以也叫熙宁变法。
在中学历史中,对王安石变法有过简要阐述。从史书中我们可以知道,王安石变法其实是一项非常杰出和先进的变法措施。这些政策虽然值得改进,但仍然对当时宋朝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那么问题又来了!司马光这样杰出的人物难道看不到变法的好处吗?他真的那么迂腐,坚持老祖宗的规律吗?
实际上,司马光反对的不是变法,而是王安石的激进变法。总的来说,王安石的政策不算太错,只是在实施的过程中,太急了。最终的结果是,新法措施不仅没有给民众带来更好的地方,反而带来了强烈的阵痛。
另一方面,在中下层官员进行政治改革时,许多人都在钻法律的空子,甚至试图从中谋取私利。这些打着变法旗号实际上在拖后腿的行为,司马光也是看在眼里的。
正是因为这种变法,人民的利益受到了损害,所以司马光才会不遗余力地反对王安石的变法措施。
司马光认为,一个好的工匠,一个好的材料,在大而不好的时候,是需要做出改变的。今天,他们两个都没有了,我害怕风雨会保护我。其实司马光的观点并没有错。由于用人不当等原因,改革实际上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从这句话,同时也可以看出,司马光不是想进行改革,而是想进行稳健的改革。循序渐进,让国家一步步适应,更有效地推进。
司马光一生最重要的两件事是:反对王安石变法,写《资治通鉴》。其实《资治通鉴》从司马光入朝就一直在进行。在宋仁宗时期,他决心编纂《通志》作为封建统治的参考。在宋英宗时期,他写了从战国到秦朝的八卷书。宋英宗审查后,他写了一个法令来更新它。
后来王安石变法轰轰烈烈,司马光无法对抗的时候,干脆选择了退让。他退休去了洛阳。在此期间,他致力于编纂《资治通鉴》,最终由宋神宗亲自执笔并命名。
是中国之一部编年通史,294卷,400多万字。这部史书主要以时间为纲,以事件为旨。成书于周威烈二十三年,止于五代后周世宗贤德六年征淮南,历十六朝,1362年。
下面分享相关内容的知识扩展:
“登州阿云案”引起的风波,从中看北宋司马光与王安石之争
话说到了神宗时,自“陈桥兵变”以来,北宋王朝已享国百余年。表面来看,经过几代人的经营,王朝似乎形势一片大好,国富民丰,朝堂人才济济,边境相对和平。且不说,仁宗朝留下的重臣如韩琦、欧阳修、富弼、文彦博均在朝,宋境之内,文化之风浓郁,一扫五代十国以来的颓势。然而在这看似一切平静之下,殊不知,大宋王朝已经在风尖浪口的前夜。饱受极大争议的“王安石变法”即将来临。无论后世怎么评论这场神宗年间的变法,大宋王朝却无法再平静下去,参与或者恰逢这场变法的人也难以置身事外,整个国家的命运夹杂着芸芸众生的命运都将以此而改变,无论你是王侯将相还是平民百姓。历史在开演之前,总会有一些小插曲,似乎是给后面的结局一些不经意的暗示。今天要说的就是一场看似不甚严重的“杀人未遂”案件,就发生在变法的前夜,然而,其所折射的背景就像暴风雨前的宁静一般。牵涉其中的两位重要人物的分歧,在此就能体现出来。这就是神宗熙宁变法的一对冤家,王安石与司马光。他们看似政敌,私底下确实好友。但是,两人都是有名的固执,无怪乎得名拗相公(王安石)与司马牛(司马光)。
这桩案子并不复杂,在《宋史》中多处都有记录,王安石传、许遵传、刑法志中均有不同程度的记述,可见这一案件的影响不同于一般。我们还原一下,看看究竟是什么分歧能让惜字如金的史书中留下多处记载。
故事发生在公元1068年,北宋熙宁元年,也就是宋神宗当皇帝的之一年。登州(今山东烟台区域)有一个女孩叫做阿云,十三四岁,古人普遍早婚,这个年纪的小姑娘也到了嫁娶之龄。阿云生得不错,现在的话说妥妥的小美女一枚。不过,阿云的身世并不美好,很小父亲的就不在了,这一年母亲突然离世。按照封建王朝礼节,应该服丧三年。父母不在只能跟着家里亲戚,但,显然亲戚并不太愿抚养,于是阿云还守丧期就将她许配给本村一名韦姓男子,姑且叫他韦大吧,订立婚约接受聘礼,于是就成了夫妻。要知道,在万恶的旧社会,婚姻之事,男女几乎不会谋面,很大程度上靠运气。阿云,一位花季少女,或许还满怀着对未来官家一些憧憬。然而很快现实就给了她一个大嘴巴子。韦大,五大三粗,相貌丑陋(“ 婿陋 ”—《许遵传》),难怪一直没找到媳妇,这次算是捡了便宜。估计,如果阿云的父母在世,见到韦大,未必会同意这桩婚事。
“心比天高,命比纸薄”,这应该就是阿云内心独白吧。然而,阿云并不甘心就这样过一生。一天,她趁着韦大熟睡之际,拿着刀想去杀他。《许遵传》中记述:“ 怀刀斫之,十余创,不能杀,断其一指。 ”显然,小姑娘没有杀人的本事,更多应该是不甘之心作祟,砍了一通,竟然只砍断一个手指头。估计,小姑娘见此景,估计是吓跑了。后来,官府来人办案时就怀疑是阿云所为,于是“ 执而诘之,欲加讯掠 ”(引同上),不认罪就要动刑,典型的粗暴式办案法。小姑娘那里经过这种场面,于是直接交代犯罪事实。杀人未遂,而且内有衷情,又发生在一个孤苦无依的小姑娘身上,以现在观点来看,触犯刑法,但量刑应该不会太重。实际上,时任登州知州的许遵也是这种观点。另外,许遵注意到,阿云订亲时,“ 母服未除,应以凡人论 ”,这是无效婚姻,所以不存在什么谋杀亲夫。而且,还有一点,虽然属于“谋杀已伤”,但阿云“ 被问即承 ”,一问就认罪,属于自首。于是就将这个案子上报,请上级部门核准执行。在宋朝,刑事案件的要一级一级上报,最终经过中央部门审核,报皇帝批准,尤其对于死刑。
很快审刑院和大理寺(国家更高司法机构,相当于现在的更高法院和更高检察院)就批驳了许遵的判决,改判 “违律为婚,谋杀亲夫”(《宋史·刑法志》) ,虽然未遂,但性质恶劣,按《宋刑统》,应处以绞刑。
注意,这里审刑院和大理寺又加了一条“违例为婚”,这条对于后面的争论也非常重要。虽然是法律规定,但这里还有道德牵涉其中,所谓礼法不分,才让案件显得复杂。
许遵收到这一判决,表示不服,于是再次上奏(负责人的父母官呀),并引用熙宁元年八月,宋神宗诏 “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从谋杀减二等论。”(《宋史·刑法志》), 以及《宋刑统•名例律》:“ 犯罪之徒,知人欲告,及按问欲举而自首陈,及逃亡之人并返已上道,此类事发,归首者各得减罪二等坐之。 ”,皇帝有诏令,律法也有依据,那么阿云不应该判处死刑;再有前面也说到了,他们的婚姻关系本身就不成立,而且许遵引律 “因杀伤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 ,案子本身就是刑事案件,与婚姻无关,不应强行绑定在一起。案子又被转到了刑部。“ 刑部定如审刑、大理 ” (《宋史·刑法志》) 直接认同审刑院和大理寺的判决。
事情到这似乎要定案了,但偏偏此时,许遵被调到了大理寺任职,他自然不同意刑部的判决,认为“ 刑部定议非直,云合免所因之罪。今弃敕不用,但引断例,一切按而杀之,塞其自守之路,殆非罪疑惟轻之义。 ”(《宋史·许遵传》)刑部不遵从皇帝敕令,而断章取义援引律条,无视阿云自首情节,所以其定议不公。所以,许遵依然坚持其原来的判法,而不认同刑部。这事被御史台(监察部门,专门负责纠错)的谏官知道了,弹劾许遵,指责他“ 妄法 ”,许遵自然不服,怎么办呢,再往上呈递吧。于是就到了皇帝那里,许遵请求皇帝召两制议。
注:鉴于宋朝官制较为复杂,我有专门文章说明这个。“两制议”是宋代的一项独特的审议机制,所谓两制是指内制的翰林学士与外制的知制诰(北宋众多名臣都在此任职过,例如大名鼎鼎的包拯、欧阳修、苏轼等等),这两个部门算起来属于皇帝的中枢秘书机构,发展成为宋朝士大夫政治的重要部分。简而言之,就是说天下有疑难案件、争议大的就由内制的翰林学士与外制的知制诰,一起讨论决定。此时的代表人物就是王安石和司马光。
对于神宗而言,其实内心里,他并不为难断,毕竟自己的态度已经体现在他的刚继位就发布的那封诏令。但是既然群臣分歧较大,还是集思广益,辩论清楚才好,另一个似乎不可告人的心思就是,测试一下群臣谁听从自己的敕令,毕竟皇帝下决心要变法图强的,须知道群臣意向,能否支持自己。《刑法志》中说王安石和司马光“ 二人议不同,遂各为奏。光议是刑部,安石议是遵 ”,两人果然意见相左,司马光支持刑部,而王安石力挺许遵,这两人的不同,实际上也代表了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与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的不同:
保守派的司马光坚持以《宋刑统》为标准,阿云必须处以绞刑,否则“ 终为弃百代之常典,悖三纲之义,使良普无告,奸凶得志,岂非徇其枝叶,而忘其根本之所致耶! ”(《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六十六,下同)正如前文所注,儒家礼法已经成为保守派的一个立论基础,“ 国家之治乱奉于礼 ”,也是司马光的一贯主张。而变法派的王安石则更重实用主义,就事论事,“ 分争辩讼,非礼不决,礼之所去,刑之所取也。 ”律法重要,按时皇帝的诏令对律法也有解释权,这点正如当今社会中更高法院对法律的解释权,具备同等效力。另外,王安石认为即使从法理上讲,阿云属于“只谋未杀”,用现在的法律术语就是“杀人未遂”,所以罪不至死。王安石还秉承其变法主张,认为“ 祖宗之法不足守 ”,并举出宋仁宗例子,“ 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数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孙当世世守之,则祖宗何故屡自改变? ”(《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五九》)
神宗一看形势,心里有数了,果然王安石是听从他的。于是很高兴,“ 诏从安石所议 ”(《刑法志》)。然而神宗还是低估了朝臣的态度,有宋一朝,对士大夫格外宽容,所以朝臣对皇帝并非如清朝之唯唯诺诺。这不,神宗诏书刚下,御史中丞滕甫上奏请再议,史记上并不同意神宗和王安石的意见,而御史钱顗(yǐ)则更进一步,要求罢免大理寺许遵。神宗甫一继位就遇到这么个难题,自己的圣旨大臣都不遵循,也是他好脾气,又下令翰林学士吕公著、韩维、知制诰钱公辅重定。吕公著等人支持王安石,神宗很高兴,下诏表示支持,并明确,“ 今后谋杀人,自首,并奏听敕裁 ”,要遵从皇帝朕的敕令。但是,事情还没结束,法官齐恢、王师元、蔡冠卿等“ 皆论奏公著等所议为不当 ”(《刑法志》)。到这个地步,朝臣有不少人依然反对,也是佩服神宗,这样还能继续下去,脾气确实太好,但显得优柔寡断了些( 注:此处就表现出神宗的性格,摇摆不定,可以料想,后面变法在大阻力下,他也不会决绝坚持。王安石被罢相,变法流产,也在情理之中 ),又下诏王安石与众法官集议,反覆论难。可见阿云案在朝廷之上,争议之大,几乎搅动整个官场。宋神宗最终采折中法,于熙宁二年八月下诏:“ 谋杀自首及按问欲举,并以今年二月二十七日敕施行。 ”原则上神宗终于肯定了王安石的结论,值此,争论了一年之久的登州阿云之案才算暂时落下帷幕。阿云的死刑得免,改判有期徒刑。后没过多久,朝廷大赦天下,阿云被释放回家。回家后的阿云又重新嫁人生子,案子 似乎 (注意,这两个字)真的结束了。这都是发生在王安石执政之后的事情了。
明眼人也能看出来,这一震动整个官场的案子,与其说是后人常论的“律敕之争”(法律与皇帝敕令),其实隐藏在背后却是不折不扣的“路线之争”或者说“政治之争”,是熙宁变法前保守派与变法派之间的小试牛刀。
王安石立论也为其变法造势,并进一步发挥,皇帝的敕令是对法律的补充与修改,拥有同样效力,这也是他获得神宗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而祖宗之法并非不可变动,要因时因势而变。
司马光坚决反对改变祖宗成法,实际上也对神宗律法解释权的反对,一旦这次“卫法”失败,也就意味着“变法”的合理性。这也是为什么即使在神宗多次下诏免除阿云死刑之后,保守势力依然不依不饶,这是他们的底线。然而,毕竟是封建王朝,一旦失去皇帝的支持,保守派必然失势。果然,变法期间,保守派悉数被闲置。
回到阿云案
前面提到,阿云案暂时尘埃落定,是在王安石执政主持变法之后,但我们知道,熙宁变法最终结果王安石两次被罢相,新法于神宗崩后,尽皆被上台为相的司马光废除。继位的哲宗皇帝就下诏:“ 强盗按问欲举自首者,不用减等。 ”这肯定是司马光的意见,也就说是,神宗当年的敕令无效。于是,这桩公案又发生了扭转。
有一个版本说,司马光掌权后,翻起这桩旧案,阿云又被逮捕并处以死刑。以司马光的个性来看,翻案很可能发生,哲宗的诏令就是佐证,因为翻案的意义在于废除新法;但是时隔十几年再将人处死,似乎显得不近人情,且在史书中也没有记述。多半是后人的编造。
再看阿云案引起的“律敕之争”与“政治之争”
今天,很多人认为,皇帝的敕令是在破坏法律,造成恶劣影响,也是北宋走下坡路的标志。其实不然,北宋“人治”政治下的法律并不同于今天的依法治国,“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从来都是停留在纸上,更不用说立法之初的不完善性。实际上,如果说皇帝的敕令合理,完全可以体现在法律上,在敕令指导下,相应不完善的条款就行修订使之完善。这与今天的法治社会概念就一脉相承。同样,“礼”的含义也不能缺失,我们常说“法律无情”,条条框框的解读可能不同,但是“以德治国”也不可或缺,结合这两年国内一些较为著名的案件(比如山东的“辱母案”,高考冒名顶替案)思考的话,我们可能会得到更加深刻的认识。以《宪法》核心,各领域分类律法共同完善的法制建设,结合“以德治国”理念,方是建设公平正义又不失活力的现代社会之路。
参考资料:
1. 《宋史》王安石传、许遵传、刑法志三等
2. “登州阿云案”中的律敕之争,李梓琳,来源万方数据
3. 宋神宗时期律敕关系考——基于对登州“阿云案”的思考,江眺,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北宋文坛大佬们的恩恩怨怨
看到这几个人的名字,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吧,他们以高超的文笔和光辉的事迹长期占据着语文课本的半壁江山,以致提到他们,那些耳熟能详的诗句和文章都信手拈来,妥妥的显示出咱也是个文化人哪。既然都是文坛大佬,后来也都身居高位,有的还当了宰相,那还有什么恩怨呢?原来,这一切都跟宋朝的变法有关,大佬们不但才华盖世,而且各个抱负不凡,都想兼济天下拯救万民,所以,问题就来了。不是我不服你,而是老大这把交椅我觉得我坐比你合适。
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
先说老大欧阳修(1007),他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考中进士,后来因为参与好哥们范仲淹的庆历新政而被贬滁州,写下了那篇有名的《醉翁亭记》,后来又渐渐得到了皇帝的信任,被留在了身边做翰林学士,负责修撰史书。与 宋祁 同修《 新唐书 》,又自修《五代史记》(即《 新五代史 》)。
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
宝元元年(1038)的时候,砸缸小能手司马光前来应考,一举得中,但因缘巧合,他与欧阳修在出京与进京的路上总是擦肩而过,闻其名未见其人,只能神交。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到了庆历二年(1042),21岁的王安石也来参加科考了,他比较低调,考中后就申请外任去做地方官了。不过欧阳修有个学生曾巩,他跟王安石是老铁,经常在欧阳修的面前提起他的好朋友,欧阳修也就对这位青年才俊另眼相看了。
嘉佑元年(1056)的时候,三十五岁的王安石觉得自己历练的差不多了,回到了京城做官,欧阳修同一年出使契丹回来,听到王安石回京的消息,非常开心,写了一首《赠王介甫》,以李白、韩愈来勉励他。
翰林风月三千首 , 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去自怜心尚在 , 后来谁与子争先。
朱门歌舞争新态,绿绮尘埃拂旧弦。
常恨闻名不相识,相逢罇酒曷留连?
王安石在收到诗后受宠若惊,立马跑去拜见了欧阳修,并且和诗一首,表达他的感慕之情:
欲传道义心犹在,强学文章力已穷。
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
抠衣最出诸生后,倒屣尝倾广座中,
只恐虚名因此得,嘉篇为贶岂宜蒙。
此后俩人亦师亦友,欧阳修说王安石的文章可做天下的表率,王安石开玩笑回应称:“我要做的是为国为民的宰相,文章只不过是拿来取乐的!”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说了这么多,该小迷弟苏轼出场了。 嘉祐 二年(1057年)二月,欧阳修做了礼部贡举的主考官,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这年,父子组合苏洵、苏轼、苏辙来报道应试了,欧阳修看到苏轼应试的文章后,非常惊喜,因担心是弟子曾巩所写,为了避嫌就选拔为第二,知道是苏轼写的后高兴的说:“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出人头地的成语也出于此。
一开始他们的关系也还是不错的,毕竟欧阳修曾经向皇帝举荐过司马光和王安石,相当于是他们的伯乐。但后来,司马光官封龙图阁直学士,王安石担任度支判官,可以说腰杆硬了,渐渐开始争夺话语权了,王安石因大宋抗辽不力写了一首《明妃曲》,表达他的不满: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
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
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
欧阳修立即和诗二首,发表他的不同意见,企图夺回领袖地位:
汉计诚已拙,女色难自夸。
明妃去时泪,洒向枝上花。
狂风日暮起,飘泊落谁家。
红颜胜人多薄命,莫怨东风当自嗟。
司马光也不甘落后,也和诗一首,发表了他的看法:
传遍胡人到中土,万一佗年流乐府。
妾身生死知不归,妾意终期寤人主。
目前美丑良易知,咫尺掖庭犹可欺。
君不见白头萧太傅,被谗仰药更无疑。
声援了欧阳修的同时对王安石进行了一番规劝。
不过毕竟都是有身份的人,君子动口不动手,他们之间的斗争也就是动动嘴皮子的文人之间的互掐,私下的交情还是不错的,经常一块喝酒唱曲拉家常是常有的事。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任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位同宰相。熙宁四年的时候,欧阳修还写了一篇《贺王相公拜相启》,对王安石当宰相表示了由衷的祝贺。但另一个人司马光就不那么爽快了。
人生只若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用牛夫人的话说就是“以前陪人家看月亮的时候,叫人家 小甜甜 ,现在新人换旧人了,就叫人家牛夫人。”王安石当宰相后,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实行青苗法、方田均税法、免疫法等,他主张“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而司马光则主张带头减俸,以开源节流的方式解决国家的财政拮据。
因私交不错,司马光刚开始以写信的方式来劝阻王安石,连写三封,到最后一封的时候,王安石不但没回,还把司马光的信念给其他人听,并且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答司马谏议书》表达自己坚决改革的决心,这下彻底惹怒了好基友司马光,两人开始了巅峰对决。
司马光上书宋神宗:“一日不罢黜新法,一日不在朝为官,冰炭岂能同炉?”王安石知道后非常愤慨,既然不能同炉,那就离的更远一点,直接将司马光发配到了战争前线陕西永兴。后来,司马光干脆挂冠辞官,声称“决口不论时事”,回到西都洛阳专心去写《资治通鉴》了。
此时欧阳修已经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了,作为保守党一派,他也成了变法改革的阻碍。在经过几次斡旋后,欧阳修自感无力劝阻,因而申请致仕回家养老了。看着自己尊敬的老师也不被待见了,小迷弟苏轼开始按捺不住,三次上书皇帝批评王安石变法,遭到了变法派的强烈反击,苏轼无奈只好自请出京,去杭州和“浓妆淡抹总相宜”的西湖为伴了。
欧阳修非常喜欢苏轼,他评价苏轼说:“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在京的时候经常邀请苏轼游玩,有一次,苏轼去欧阳修家做客,欧阳修指着窗外的柳树对苏轼说: “墙边柳,枕边妻,无叶不青,无夜不亲。” 要求苏轼对出下联,苏轼看着笼子里的鸟立即说: “笼中鸟,仓中谷,有架必跳,有价必粜。” 惹的欧阳修哈哈大笑。后来,还将自己的孙女嫁给了苏轼的二儿子,成了亲家。
外任期间,苏轼看到青苗法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又上书进谏,奈何还是不被重视,王安石因此评价他说:“华才诚无用,有吏材则能治人。”
所幸苏轼天生阔达,既然不受重视,那就寄情山水,多做点实事吧。后来又去密州做官,写下了那首很有名的《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
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王安石虽然铁腕治国,但还是经不住保守势力的一次次反击,终于在熙宁九年(1076年)因病请辞,再也不想做这个费力不讨好的宰相了,回到故乡开始隐居。即使这样,也没改变他不畏强权的决心。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轼由 徐州 调任湖州,写了一封感谢皇帝的奏折,没想到却引发了杀身之祸,制造了宋朝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司马光、欧阳修都被牵连。
眼见人头落地,这时远在钟山的王安石向皇帝投了关键的一票反对票,“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看来还是友情可贵啊,苏轼因此没被杀头而贬去了黄州。到黄州后,他就近去看望了赋闲在家的王安石,两人同游钟山,畅谈时事,冰释前嫌。王安石还写了一首诗《北山》:
北山输绿涨横玻,直堑回塘滟滟时。
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
苏轼也更加了解王安石的为人,后来他逢人就称赞王安石说:“不知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在黄州期间,苏轼在游览景色的时候,想起了老师欧阳修,写下《 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 》,表达对老师欧阳修的思念。
落日绣帘卷,亭下水连空。
知君为我新作,窗户湿青红。
长记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杳杳没孤鸿。
认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 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
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
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
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王安石变法期间,一脚踢开了好基友司马光,外任了苏轼,没想到这俩人却在患难之中惺惺相惜起来。早在京城期间,司马光作为苏轼的上司,就曾为苏轼的母亲写过墓志铭,也曾经在皇帝面前为苏轼苏辙兄弟说过话,所以他们也是有一定的感情基础的。
苏轼在密州的时候,修建了一座超然台,由他的弟弟苏辙写了一篇《超然台赋》,他自己写了一篇《超然台记》,这些作品连同苏轼的其它诗作传到司马光手里。熙宁十年苏拭任徐州太守前夕,收到了司马光写的《超然台诗寄子瞻学士》,诗中称颂苏轼:
使君仁知心,
济以忠义胆,
婴儿手自抚,
猛虎须可搅。
出牧为龚黄,
廷议乃陵黯,
万钟何所加,
儋石何所减。 .
为了回报司马光,苏轼一到徐州,就给司马光回了一首《司马君实独乐园》:
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
中有五亩园,花竹秀而野。
花香袭杖屦,竹色侵盏斝。
樽酒乐余春,棋局消长夏。
洛阳古多士,风俗犹尔雅。
先生卧不出,冠盖倾洛社。
虽云与众乐,中有独乐者。
才全德不形,所贵知我寡。
不仅高度赞扬了司马光在洛阳买的豪宅,还说“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天下的人都知道司马光的名气,劝他出山参与政治,造福百姓,嘲笑他“抚掌笑先生,年来效喑哑。”这首诗在乌台诗案中也被当做证据,司马光因此也收到牵连,被罚铜二十斤。苏轼大难不死贬去黄州后,写信给司马光表达自己的内疚之情。
然而,人生总是也无风雨也无晴。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去世, 宋哲宗 赵煦 即位,改元元祐,由太皇太后高氏 垂帘听政 。高太后在神宗时就强烈反对变法,等到自己听政后,立即起用 司马光 为相。司马光怎能忘了这位患难兄弟呢,到任一年内便火箭式提拔苏轼,让他回朝做了中书舍人、翰林学士。
原以为这下苦尽甘来,好兄弟可以共扶明主匡治天下了,问题又来了。元祐元年,司马光全面叫停新法,但苏轼却认为新法有利有弊,不应当一刀切,两人常常因为这件事争的面红耳赤,互不相让。苏轼曾经在散朝后气的大骂:“司马牛,司马牛。”而远在金陵的王安石听到新法被废的消息后气的发疯,半年后就一命呜呼了。
苏轼因为与司马光政见不合,又受到了保守党派的攻击,无奈之下又自请出京,去杭州做知州了。比不过当官还比不过写诗吗?大文豪信手拈来,写了一首回文诗:
《菩萨蛮回文夏闺怨》
柳庭风静人眠昼,昼眠人静风庭柳。
香汗薄衫凉,凉衫薄汗香。 手红冰碗藕,藕碗冰红手。
郎笑藕丝长,长丝藕笑郎。
司马光在担任宰相一年多之后,也因为在无穷无尽的党争中心力交瘁而死。而为他写祭文的事自然落到了苏轼头上,他在《祭司马君实》中很公允的评价了司马光历任四朝的功绩,又在《安葬祭文》中说司马光“明高当世,行满天下”,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纵观四人一生的事迹和交往,欧阳修于他们来说是老师与伯乐,充当了领路人,恩深怨也浅。他们之间的恩怨,其实也是在国家大义与个人原则方面都棱角分明,坚持自己的主张,并非私人恩怨。四人中,苏轼年龄最小,所受人生波折也最多,但他却能一概豁达面对,“为米折腰,因酒弃家,口体交相累”而毫无怨言,在三位故去后为他们撰写墓志,前往吊唁。真正的领悟到了“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真谛。
注:图片来源于网络
大宋因为司马光废除了王安石15年变法,而受到了什么影响?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发送邮件至 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